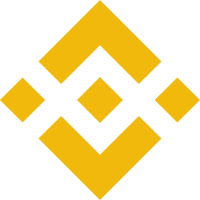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北岸犬舍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北岸城养狗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本文目录
北城以北的其他信息求11月最小说《北城以北》全文北城以北的其他信息北城以北作者:余慧迪
我从祖国的最东南处起,一路向北逃离,逃到北城以北的地方。
——前记
北城在木棉、荔枝和紫荆的混合香气的熏陶下,渐渐地有些昏昏欲睡了。
从前北城人只知道他们世代居住的这座小城在H城的北部,又在东江下游的北岸,于是为其命名曰:北城。到后来,北城人终于知道,北城原来坐落在祖国东南的广东省,又隶属于广东省东南部H市,相当于国土的最东南端。然而这名字叫得久了也就习惯了,于是北城一直叫北城。
北城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H城西北部,南望东莞,毗邻港澳,靠近广州、香港、深圳。照理说,这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有利于发展的,可是北城有些慵懒,有些倦怠。眼见得深圳、东莞这些邻居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如火如荼地搞改革,现在一个个经济都发展得如日中天了,北城仍旧是懒懒地,翻一翻身,挠一挠痒,继续晒它的太阳。
我的家在临近东江的一个住宅区里。幢幢相同的房子、相差无几的紫荆、大块单调的空地,组成了一个平凡的小区。十几年来小区就没出过事,风平浪静。
那个普通的星期五下午,我从学校一路狂奔回家,一把把书包甩在地板上,就冲到阳台门口。文心兰总是在下班之后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打理她种的吊兰。一盆盆的兰草悬挂在阳台上空,叶子细长优美,嫩绿之中夹着一线鹅黄,勾着半圆的弧线,风一吹过便摇曳生姿。
文心兰像平时一样给吊兰浇水。她用拈花指扶着水壶,微微倾斜,水小股儿小股儿地汇到花盆里。我默不做声地直盯着她。她的头隐没在十几盆吊兰中间,我只看到一只漆黑的眼睛在嫩绿和鹅黄中闪了一下,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咒骂:“掐死你那双黑眼珠子哦,瞪得跟死人似的。”
我很响亮地吸了下鼻子,努力使自己的眼睛看起来不那么水汪汪。那些盈满的泪珠似乎一不小心就会纷纷滚下来。“小柒哪里去了?”我问。
“瞧你那死样儿,什么小柒,哪个死人啊。”文心兰继续歹毒地说着。
我又下了一番极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我是问,莫柒信哪里去了?”
“死在外面了。”她继续面不改色,一如既往地用冷漠把我的焦虑击溃。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声音软下来,用一种卑怯惶恐的声音可怜巴巴地问:“妈妈,我能不能求你告诉我莫柒信到底去哪儿了?”
“求我?你这死丫头这是在求我吗?为了一个臭不要脸的死人求我?”文心兰关节发白地攥住一盆吊兰。她摇晃得那样厉害,以至于那么多细弱的叶子也跟着瑟瑟发抖。啪的一声。一颗炸弹擦着我的左耳爆炸。陶瓷和泥土纷纷扬扬地落了我一身,几根细长的叶子滑稽地耷拉在我肩上。我一边扯起书包冲回房间,一边摔上门,靠在墙角把头埋进膝盖里嘤嘤地小声哭泣起来。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渴望逃离北城,逃离这个噩梦。
在我尚年幼就意识到文心兰的说话方式是多么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也不禁注意到大多数北城人也有着跟她相同的习惯。他们说话特别钟爱一个“死”字,名词前加“死”,动词前加“死”,宾语前加“死”,一切可以加上这道装饰的地方,他们都会毫不客气地赋予一个“死”字。比如仅仅是因为回家晚了这样一件小事,文心兰也可以用极其壮烈的方式把我责骂个狗血淋头:“死丫头,也不用你那双死眼看看现在几点了,你老实交代你死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知道死回家?活得太舒服想死了是吧?下次你再这么晚死回来看我不揍死你。”
这件事我倒不怪她。因为在她背后,有整个北城的八十多万人为她作了铺垫。
北城是个充满怨气的地方。我一直这么觉得。北城人有一个特殊的本事,无论大小事,他们总能从客观上找原因。比如天气不好,比如时间不对,比如张三太贪小便宜或者李四太蛮不讲理。只要稍稍沾上点边儿的理由,不管有理没理都会成为冠冕堂皇的真理,以此来作为他们成绩不好、生意不好或者运气不好的最好的解释。年轻人到处大骂特骂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烦人的家长;老人们在大树下乘凉赶蚊,顺便数落不肖的子孙;女人们提着大袋小袋穿越在肮脏的市场里,嘴里忙着咒骂持续上涨的价格和小贩们缺斤少两的卑劣行为。上班族们抱怨昂贵的石油和低迷的股市。如此这般,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自打我懂事以来,最早是从外祖母那里懂得了怨怒的害处。我的外祖母祖籍深圳,当年她只有五六岁的年纪,被一颗话梅糖轻易地骗到了北城。长途汽车上的奔波劳累以及一脸恶相的人贩子,吓得她不会说话,在卖入文家以前,一直都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面目慈祥的文老爷子把她的手轻轻放在他宽厚的大掌上面,问她的名字,她唯有拼命地摇头。于是老人又把她的小手转交给了另一只小手。
年轻的文家少爷宽厚老实,问她,“我叫文景森。你叫什么名字?”
她依旧只摇头。过了一个月,才开口说话。“玲玲。”她卑怯地小声说道。
“哪个?是王令玲,还是王林琳,又或者灵气的灵?”
她复摇头。文景森继续耐心地问:“那你姓什么?”
她伸出一只食指,在空中画了三横,再一竖。他笑,从此替她取名为王玲。
起初那段日子,他继承了祖上的家业。文家世代做木工,于是他的名字里有三木。凭着一双巧手和憨厚善良的品格,他很快把产业做得更大,财富累积得更多。闲暇时光,他也教她写字,一横,再一横,笔笔遒劲有力。
王玲一辈子只学会写四个字:一、二、三,以及她的姓氏,王。
文家本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她又是买进来的童养媳,更不需什么文化。很多时候,她想起他教她写字的样子,不自觉地兀自动动食指,一横,一横,再一横,然后是狠狠的一竖。她便得意地嘿嘿笑开来。
那是夫妻俩一段平淡的幸福时光。后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他的财产收入公社。出于对祖业的热爱和尊敬,他偷偷留了一台刨木的机床。被揭发后,他被揪到大街上狠狠地批斗。接着是一段最黑暗无边的苦日子。她从阔绰的文家少奶奶变成了公社里面煮饭的厨娘。每天起早摸黑,与柴火和煤烟为伴。
外祖母很喜欢跟我们讲起以前的故事,说她自己的遭遇,也说一些听来的恐怖故事。到了最后,每每都是她不能自制地嘶喊:“凭什么?那么多年的艰难都熬过来了,他凭什么就在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撒手归去留我一人在世?凭什么!”
而最近的这十几年,外祖母又多了一条新的理由去怨恨:那就是她的故乡深圳。她眼睁睁地看着生她并且原本应该育她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享誉国际的现代化大城市,而她所在的北城居然还漫不经心地用散步一样的速度慢慢发展。她简直愤怒了。
“凭什么?我原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过上更好的生活,凭什么要我沦落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一辈子?”她怨人贩子,怨文家老太爷,怨文景森,怨批斗他的人们,怨整个北城。
但是我发现,她唯独忘记了责备自己,当年为何嘴馋得为了一颗糖就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祖母心脏不好,大概就是被怨念所侵蚀的。
王玲在来到北城的第十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接下来是第二个,第三个。
1967年初,正值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日,大年三十那一晚,大腹便便的王玲在做年夜饭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倒在了灶台边。
当晚,文心兰出生。由于是最小的孩子,又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文景森非常偏爱这个孩子。他常常把她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带着她到处晃;又用胡茬把她弄得咯咯笑。文心兰从小就受到了与那个年代不符合的宠爱,比如上小学时就穿着时髦的方格连衣裙吸着牛奶咬着饼干去上学。
可以想见,文心兰从小就对父亲过分地依恋和亲密。而四个孩子里面,只有三哥文尹城最像父亲。尹城不仅活泼聪明,而且风度翩翩。在那个叛逆的年纪,文尹城不仅是文心兰最喜爱的哥哥,更是她心目中关于男性的全部楷模。
然而文尹城的风光只持续到了十八岁。一场高考把他的骄傲击垮了,在家唉声叹气了两个月之后,他走上了复读之路。而文心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决定继续升读高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她亲爱的哥哥。
文尹城重考了三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连他的妹妹也高中毕业了。但她没有考上大学。他临上大学前慈爱地抚摸着她的头说:“丫头,乖乖等我。要听话。”
她当真听话地等了他四年。那四年里她在乡下小学里教书,拿着微薄的薪水,怀着厚实的梦想。她在黄昏的狗尾巴草丛边上学会了弹吉他,穿着格子衬衣,乌黑的头发盖着半张脸,对着橘红的夕阳轻轻地笑红了脸。
四年之后,她褪去了青涩,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姑娘。四年后他回来,出落得更加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手上还挽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叫石榭兰,在电视台混了几年仍混不出名气的小明星。
她争着出门去迎接他,听着他熟悉的声音亲昵地喊着“兰兰”,却错愕地发现,那人不是自己。那么突兀地,她的身心凉透。“狐狸精!”她暗暗地骂,转身跑回了房。
打那以后,年轻的文心兰也成了一个有怨的女人。
所有的哥哥姐姐都谈婚论嫁了。文心兰在家里倒像是个怨妇。她大声地抱怨,抱怨电视台的节目太无聊,抱怨大哥的孩子吵吵闹闹,抱怨嫂子的香水喷得太多——她尖锐刻薄的话语给家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困扰。文尹城提议说该给他这个宝贝妹妹找个人家了。
王玲早在文心兰高中毕业时就曾经给她找了个婆家,男方姓莫,是当地一个老实巴交的个体户。当时她坚持要下乡教书,推掉了。婚约书还在家里那个大立柜的底层。文心兰把它翻出来,一个人偷偷去了莫家。
“你还娶不娶我?”她大着胆子问。
莫凌忠被她吓住了:“你一推就是四年……我已经有老婆孩子了……”
“那这份婚约书怎么办?”她扬起手中的武器。
客厅外面的林秀娥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冲进去,扬手给了她一巴掌。
后来,文心兰渐渐走出了哥哥的阴影。半年后,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公务员裴辰。再后来,她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儿,从此开始了我在人间噩梦般的记忆。
我叫裴飞,出生在北城最美的季节。那时木棉花尚未落尽,紫荆刚刚抽出花苞。早熟的荔枝在街头零星可见,颗颗棱角分明。
大人们都说我从小颖慧,刚入学就跳级,年年捧回厚厚的奖状。乖巧、缄默,看上去很安静。我从小在文心兰的严格监管下长大,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忍受一句话里夹着好几个“死”字的咒骂,学会了低着头急速穿过骂街的女人和睡着的乞丐。平和地等待和无限地忍耐是我的本领,在北城里任何人都必须学会忍耐再忍耐,否则就只能成为在街上破口大骂的市侩女人,或者庸俗无能的男人,直到成为碎碎念着怨毒的故事的老人。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离开北城,向北逃亡,远远地离开这片怨气丛生的地方。
在早年的观察中,文心兰早早断定我没有学音乐和美术的天赋,就果断地把我踹到了应试教育的路上。我从六岁起开始戴厚厚的眼镜看厚厚的书本,为老师所疼爱为同学所不齿。正因如此,我没有没心没肺的死党,没有可以交心的密友。只有小柒。在北城的时节,他陪我拾过木棉,摘过紫荆,在放学的路上分享过一串荔枝。
“以后我们一起离开北城吧。”他看着满树火焰一样的木棉,好似不经意地说。
“什么时候?”我激动地问。
“快了,快了……我们都快十二岁了,我想……”他的话语渐渐低下去,低下去,湮没在一片深红里。一朵饱满的木棉花“啪”的一声掉落在我面前,惊碎了我的幻想。
“走吧。”
那是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我把小柒邀请到了我的生日会上。文心兰和爸爸都对乖巧的小柒印象很好,一留再留,最后天色已晚,爸爸提出要送他回家。小柒说:“不用了,我爸爸正在赶来,应该快到了。”
门一开,文心兰怔了半分钟。她把门掩上,脸色发青地对小柒说:“小柒,你全名叫什么?”
“莫柒信。柒是大写的‘七’,信是……”
“‘讲信用’的‘信’。”林秀娥咬牙切齿地在门后回答,身后是目瞪口呆的莫凌忠。
“不讲信用的是你吧?”文心兰冷哼一声,把小柒推出门去。“柒,我们走!不要再到这个女人家里!”林秀娥嫌不解气,又转过身向我们家歇斯底里地吼,“死不要脸!”
我在猫眼后可怜巴巴地望着小柒离开的背影,心里盘算着明天去上学时怎么跟他解释。
然而无须我绞尽脑汁地想一个妥当的解释,因为小柒没有来上学。
我没有从文心兰处得知我想要的结果。小柒从此没有再在北城出现过。而我在十三岁后,也毅然到外面求学去了。文心兰、外祖母、林秀娥,上一代以及上上一代的人们依然待在北城——生他们养他们给了他们血肉的北城。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都和北城完美契合,密不可分。他们一辈子离不开这座小城。
一条弯弯的东江支流形成了天然屏障,把陈旧的北城和繁华的H市隔绝开来。北城里面有很多年代较久的住宅区,建在江边,仅仅隔着一道青赭色的老城墙就与东江水相接。
但和外面的H市,和整个欣欣向荣的珠三角不同,北城那样安逸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年岁,不争不取。在一棵棵古榕、一道道古墙、一阵阵催人入睡的暖风中,悠然地躺在水面上歇息。
但是北城的人们还会不时说起,为何同是人,同喝一条江的水,我们和深圳人、香港人的命运就相差那么大呢?他们说起的时候,依旧是“死”字连篇的句式,依旧是恶毒怨恨的语气,依旧是懒洋洋的表情。
评委郭敬明点评:
余慧迪的文字,在所有参赛者里面,显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和辛辣。整个文章从结构到叙述,充斥着一种跳出故事本身和作者经历的冷漠感,所有评委在看到这篇《北城以北》的时候,都无法相信这样的佳作出自仅仅十六岁的小女孩之手。我甚至有种预感,如果她每一次比赛的发挥都保持这个水准的话,她极有可能问鼎“文学之新”的冠军。她是目前为止,我在比赛里看见的最大的黑马。
本文作者作品收录于:
《第一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作品全集(上)》
《第二届「THE NEXT·文学之新」优秀入选作品集》
求11月最小说《北城以北》全文北城以北
我从祖国的最东南处起,一路向北逃离,逃到北城以北的地方。
——题记
北城在木棉,荔枝和紫荆混合香气的熏陶下,渐渐地有些昏昏欲睡了。
从前北城人只知道他们世代居住的这座小城在H城的北部,又在东江下游的北岸,于是为其命名曰:北城。到后来,北城人终于知道,原来北城坐落于祖国东南的广东省,又隶属于广东省东南部H市,相当于国土的最东南端。然而这名字叫得久了也就习惯了,于是北城一直叫北城。
北城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H城西北部,南望东莞,毗邻港澳,靠近广州,香港,深圳。照理说,这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有利于发展的,可是北城有些慵懒,有些倦怠。眼见得深圳,东莞这些邻居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如火如荼地搞改革,现在一个个经济都发展得如日中天了,北城仍旧是懒懒地翻一翻身,挠一挠痒,继续晒它的太阳。
我的家在临近东江的一个住宅区里。幢幢相同的房子,相差无几的紫荆,大块单调的空地,组成了一个平凡的小区。十几年来小区就没出过事,风平浪静。
那个普通的星期五下午,我从学校一路狂奔回家,把书包甩在地板上,就冲到阳台门口。文心兰总是在下班之后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打理她种的吊兰。一盆盆的兰草悬挂在阳台上空,叶子细长优美,嫩绿之中夹着一线鹅黄,勾着半圆的弧线,风一吹过便摇曳生姿。
文心兰像平时一样给吊兰浇水。她用拈花指扶着水壶,微微倾斜,水小股小股地汇到花盆里。我默不作声地直盯着她。她的头隐没在十几盆吊兰中间,我只看到一只漆黑的眼睛在嫩绿和鹅黄中闪了一下,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咒骂:“掐死你那双黑眼珠子哦,瞪得跟死人似的。”
我很响亮地吸了下鼻子,努力使自己的眼睛看起来不那么水汪汪。那些盈满的泪珠似乎一不小心就会纷纷滚落下来。“小柒哪里去了?”我问。
“瞧你那死样,什么小柒,哪个死人啊。”文心兰继续歹毒地说着。
我又下了一番极大的努力,才染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我是问,莫柒信哪里去了?”
“死在外面了。”她继续面不改色,一如既往地用冷漠把我的焦虑击溃。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声音软下来,用一种卑怯惶恐的声音可怜巴巴地问:“妈妈,能不能求你告诉我莫柒信到底去哪儿了?”
“求我?你这死丫头这是在求我吗?为了一个臭不要脸的死人求我?”文心兰关节发白地攥住一盆吊兰。她摇晃得那样厉害,以至于那么多细弱的叶子也跟着瑟瑟发抖。啪的一声,一颗炸弹擦着我的左耳爆炸。陶瓷和泥土纷纷扬扬地落了我一身,几根细长的叶子滑稽地耷拉在我肩上。我一边扯起书包冲回房间,一边摔上门,靠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嘤嘤地小声哭泣起来。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渴望逃离北城,逃离这个噩梦。
在我尚年幼时就意识到文心兰的说话方式是多么不同的时候,我也不禁注意到大多数北城人也有着跟她相同的习惯。他们说话特别重爱一个“死”字,名词前加“死”,动词前加“死”,宾词前加“死”,一切可以加上这道装饰的地方,他们都会毫不客气的赋予一个“死”字。比如仅仅是因为“回家晚了”这样一件小事,文心兰也可以用极其壮烈的方式把我责骂个狗血喷头:“死丫头,也不用你那双死眼看看现在几点了,老实交代你死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知道回家?活得太舒服想死了是吧?下次你再这么晚回来看我不揍死你!”
这件事我倒不怪她。因为在她背后,有整个北城的八十多万人为她做铺垫。
北城是个充满怨气的地方。我一直这么觉得。北城人有一个特殊的本事,无论大小事,他们总能从客观上找到原因,比如天气不好,比如时间不对,比如张三太贪小便宜或者李四太蛮不讲理。只要稍稍沾上点边的理由,不管有理没理都会成为冠冕堂皇的真理,以此来作为他们成绩不好、者运气不好的最好解释。年轻人到处大骂特骂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烦人的家长;老人们在大树下乘凉赶蚊,顺便数落不孝的子孙;女人们提着大包小袋穿越在肮脏的市场里嘴里忙着骂持续上涨的价格和小贩们缺斤少两的卑劣行为;上班族们抱怨昂贵的石油和低迷的股市。如此这般,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我自打懂事以来,最早是从外祖母那里懂得了怨怒的害处。我的外祖母祖籍深圳,当年她只有五六岁的年纪,被一根话梅糖轻易的骗到了北城。长途汽车的奔波劳累以及一脸恶相的人贩子,吓得她不会说话,在卖入文家以前,一直都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面目慈祥的文老爷子把她的手轻轻放在自己宽厚的打掌上面,问她的名字,她唯有拼命地摇头。于是老人又把她的小手转交给了另一只小手。
年轻的文家少爷宽厚老实,问她:“我叫文景森。你叫什么名字?”
她依旧只是摇头。过了一个月,才开口说话。“玲玲。”她卑怯的小声说道。
“哪个?是王令玲,还是王林琳,又或者是灵气的灵?”
她复摇头。文景森继续耐心的问:“那你姓什么”
她伸出一只食指,在空中画了三横,再一竖。他笑,从此替她取名为王玲。
起初那段日子,他继承了祖上的家业。文家世代做木工,于是他的名字里有三木。凭着一双巧手鹤憨厚善良的品格,他很快把产业做得更大,财富累积的更多。闲暇时光,他也教她写字,一横,再一横,笔笔遒劲有利。
王玲一辈子只会写四个字:一、二、三,以及她的姓氏,王。
文家本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她又是买进来的童养媳,更不需什么文化。很多时候,她想起他教她写字的样子,不自觉的兀动动手指,一横,一横,再一横,然后是狠狠的一竖。她便得意的嘿嘿笑开来。
那是夫妻俩一段平淡的幸福时光。后来,“一大二公”的人民文化社运动兴起,他的财产收入公社。出于对祖业的热爱和尊敬,他偷偷留了一刨木的机床。结果被揭发,揪到大街上狠狠的批斗。接着是一段最黑暗无边的苦日子。她从阔绰的文家少奶奶变成了公社里面煮饭的厨娘。每天起早摸黑,与柴火和煤烟为伴。
外祖母很喜欢跟我们讲起以前的故事,说她自己的遭遇,也说一些听来的恐怖故事。到了最后,每每都是不能自制的嘶喊:凭什么?那么多年的艰难都熬过来了,他凭什么就在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撒手归去留我一个人在世?凭什么!
而最近的十几年,外祖母又多了一条新的怨恨理由,那就是她的故乡深圳。她眼睁睁的看着生她并且原本应该养育她的小渔村如今变成了享誉国际的现代化大城市,而她所在的北城居然还漫不经心的用散步一样的速度慢慢发展。她简直愤怒了。
”凭什么?我原本应该有更好的条件,过上更好的日子,凭什么要我在这个小城市里面窝囊一辈子?”她怨人贩子,怨文家老太爷,怨文景森,怨批斗他的人们,怨整个北城。
但是我却发现,她唯独忘记了责备自己,当年为何嘴馋得为了一根糖就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祖母心脏不好,大概就是被怨念所侵蚀的。
王玲在来到北城的第十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接下来是第二个,第三个。
1967年初,正值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日,大年三十那一晚,大腹便便的王玲在做年夜饭时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痛,倒在了灶台边。
当晚,文心兰出生。由于是最小的孩子,又是个白白净净的的小姑娘,文景森非常偏爱这个孩子。他常常把她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带着她到处晃;又用胡茬把她弄得咯咯笑。文心兰从小就受到了与那个年代不符合的宠爱,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就穿着时髦的方格裙吸着牛奶咬着饼干去上学。
可以想见,文心兰从小就对父亲有着过分的依恋和亲密。而四个孩子里面,只有三哥文尹城最像父亲。尹城不仅活泼聪明,而且风度翩翩。在那个叛逆的年纪,文尹城不仅是文心兰最爱的哥哥,更是她心目中关于男性中的全部楷模。
然而文尹城的风光只持续到了十八岁。一场高考把他的骄傲击垮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两个月以后,他走上了复读之路。而文心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决定继续升读高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她亲爱的哥哥。
文尹城重考了三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连他的妹妹也高中毕业了,但她没有考上大学。他在上大学前慈爱的抚摸着她的头说,“丫头,乖乖等我。要听话。”
她当真的听话地等了他四年。那四年她在乡下小学里教书,拿着微薄的薪水,怀着厚实的梦想。她在黄昏的狗尾巴草丛边学会了弹吉他,穿着格子衬衣,乌黑的头发盖着半张脸,对着橘红的夕阳轻轻地笑红了脸。
四年之后,她褪去了青涩,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姑娘。四年后他回来,出落得更加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手上还挽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叫石榭兰,在电视台混了几年还混不出名气的小明星。
她争着出门去迎接他,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亲切的喊着“兰兰”,却错愕的发现,那人不是自己。那么突兀的,她的身心透凉。“狐狸精!”她暗暗的骂,转身跑回了房。
打那以后,年轻的文心兰也成了一个有怨的女人。
年轻的文家少爷宽厚老实,问她:“我叫文景森。你叫什么名字?”
她依旧只是摇头。过了一个月,才开口说话。“玲玲。”她卑怯的小声说道。
“哪个?是王令玲,还是王林琳,又或者是灵气的灵?”
她复摇头。文景森继续耐心的问:“那你姓什么”
她伸出一只食指,在空中画了三横,再一竖。他笑,从此替她取名为王玲。
起初那段日子,他继承了祖上的家业。文家世代做木工,于是他的名字里有三木。凭着一双巧手鹤憨厚善良的品格,他很快把产业做得更大,财富累积的更多。闲暇时光,他也教她写字,一横,再一横,笔笔遒劲有利。
王玲一辈子只会写四个字:一、二、三,以及她的姓氏,王。
文家本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她又是买进来的童养媳,更不需什么文化。很多时候,她想起他教她写字的样子,不自觉的兀动动手指,一横,一横,再一横,然后是狠狠的一竖。她便得意的嘿嘿笑开来。
那是夫妻俩一段平淡的幸福时光。后来,“一大二公”的人民文化社运动兴起,他的财产收入公社。出于对祖业的热爱和尊敬,他偷偷留了一刨木的机床。结果被揭发,揪到大街上狠狠的批斗。接着是一段最黑暗无边的苦日子。她从阔绰的文家少奶奶变成了公社里面煮饭的厨娘。每天起早摸黑,与柴火和煤烟为伴。
外祖母很喜欢跟我们讲起以前的故事,说她自己的遭遇,也说一些听来的恐怖故事。到了最后,每每都是不能自制的嘶喊:凭什么?那么多年的艰难都熬过来了,他凭什么就在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撒手归去留我一个人在世?凭什么!
而最近的十几年,外祖母又多了一条新的怨恨理由,那就是她的故乡深圳。她眼睁睁的看着生她并且原本应该养育她的小渔村如今变成了享誉国际的现代化大城市,而她所在的北城居然还漫不经心的用散步一样的速度慢慢发展。她简直愤怒了。
”凭什么?我原本应该有更好的条件,过上更好的日子,凭什么要我在这个小城市里面窝囊一辈子?”她怨人贩子,怨文家老太爷,怨文景森,怨批斗他的人们,怨整个北城。
但是我却发现,她唯独忘记了责备自己,当年为何嘴馋得为了一根糖就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祖母心脏不好,大概就是被怨念所侵蚀的。
王玲在来到北城的第十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接下来是第二个,第三个。
1967年初,正值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日,大年三十那一晚,大腹便便的王玲在做年夜饭时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痛,倒在了灶台边。
当晚,文心兰出生。由于是最小的孩子,又是个白白净净的的小姑娘,文景森非常偏爱这个孩子。他常常把她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带着她到处晃;又用胡茬把她弄得咯咯笑。文心兰从小就受到了与那个年代不符合的宠爱,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就穿着时髦的方格裙吸着牛奶咬着饼干去上学。
可以想见,文心兰从小就对父亲有着过分的依恋和亲密。而四个孩子里面,只有三哥文尹城最像父亲。尹城不仅活泼聪明,而且风度翩翩。在那个叛逆的年纪,文尹城不仅是文心兰最爱的哥哥,更是她心目中关于男性中的全部楷模。
然而文尹城的风光只持续到了十八岁。一场高考把他的骄傲击垮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两个月以后,他走上了复读之路。而文心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决定继续升读高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她亲爱的哥哥。
文尹城重考了三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连他的妹妹也高中毕业了,但她没有考上大学。他在上大学前慈爱的抚摸着她的头说,“丫头,乖乖等我。要听话。”
她当真的听话地等了他四年。那四年她在乡下小学里教书,拿着微薄的薪水,怀着厚实的梦想。她在黄昏的狗尾巴草丛边学会了弹吉他,穿着格子衬衣,乌黑的头发盖着半张脸,对着橘红的夕阳轻轻地笑红了脸。
四年之后,她褪去了青涩,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姑娘。四年后他回来,出落得更加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手上还挽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叫石榭兰,在电视台混了几年还混不出名气的小明星。
她争着出门去迎接他,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亲切的喊着“兰兰”,却错愕的发现,那人不是自己。那么突兀的,她的身心透凉。“狐狸精!”她暗暗的骂,转身跑回了房。
打那以后,年轻的文心兰也成了一个有怨的女人。
好了,关于北岸犬舍和北岸城养狗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